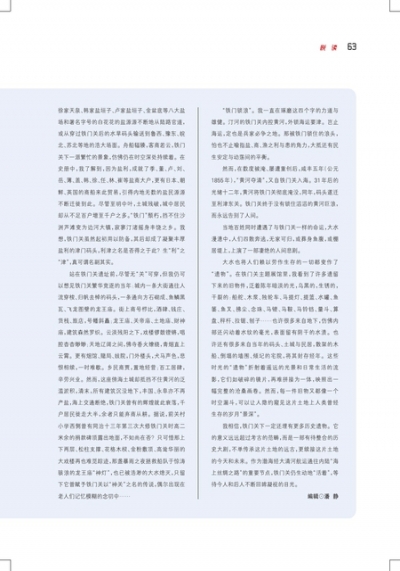文王 川
在那片土地上游荡的时候,我注意到,很多人把目光投向汀罗镇的铁门关,那是利津历史上的第一名胜。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它早已被淤沙深埋地下,再也看不到一丝痕迹。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很可能会变作一个传说,变作后人心生遗憾的推测与想象。即使今天,它也已然变形为纸页上抽象的符号,只散存于县志和文史资料中,再不能从文字上耸立起来,与人们的推测与想象对接、呼应、印证。铁门关,如此坚硬的存在也能被时光破为齑粉吗?时间的力量真是强大。
铁门关何时建成,似无具体年代可考,若从金代算起,约有七百余年。当地有种说法:先有铁门关,后有利津城。这很符合人类因利而逐、因利而居的天性,何况此地所出,实有大利。而这里最繁华的时候当在明清两代,之前的铁门关,更多的功能在于海防。《利津县志》和《中国古今大辞典》均有记载,称其“金置,明设千户所,以资防御,有土城遗址”“形势雄伟”。金政府为控海滨之险,建筑土城,方圆近五里,四方各有巨大城门,门上有铁环、满布铁钉,“铁门”之称由此而来(据崔树梓口述、李钧整理《铁门关》)。其时,县城西北七十里的丰国镇濒临渤海,有自然盐沟,盐业发达,来往商船、渔船时停泊于此,铁门关便也兼有了航运码头的功能。“举棹而获鱼鲜,泛舟则获盐利。”加之关东三粮的输入,其贸易繁荣,自不待言。“蛎浦朝宗,济水达于千里;铁门锁浪,沧海长于百川。”(《武定府志》)如此气魄伟阔、盐渔丰饶之地,怎能不富甲一方、强盛一隅?
多次去过利津,“铁门关”是当地人口中频现的词汇,不断引发我的神往。有时候在茫茫夜色中散步,我会猜想铁门关在哪个方向、距我多远。会不会在我行走的乡路上或不远处,就有当年熙来攘往的人流与马车队前来经商、运盐的繁忙景象,他们如一溜烟云般出入铁门关口,嘈杂的吆喝、辚辚的车声和萧萧的马嘶缭绕不绝,响彻云霄。我想象着那些来自淄川的盐商许氏、来自杭州府仁和县的丰国盐场大使纪氏,还有无数外地盐民、盐商,将盐窝场、永阜场、丰国场、徐家天泉、韩家盐垣子、卢家盐垣子、金盆底等八大盐场和著名字号的白花花的盐源源不断地从陆路官道,或从穿过铁门关后的水旱码头输送到鲁西、豫东、皖北、苏北等地的浩大场面。舟船辐辏,客商若云,铁门关下一派繁忙的景象,仿佛仍在时空深处持续着。在史册中,我了解到,因为盐利,成就了季、董、卢、刘、岳、薄、盖、韩、徐、任、林、崔等盐商大户,更有日本、朝鲜、英国的商船来此贸易,引得内地无数的盐民源源不断迁徙到此。尽管至明中叶,土城残破,城中居民却从不足百户增至千户之多。“铁门”颓朽,挡不住沙洲芦滩变为边河大镇,寂寥汀渚摇身丰饶之乡。我想,铁门关虽然起初用以防备,其后却成了凝聚丰厚盐利的津门码头,利津之名是否得之于此?生“利”之“津”,真可谓名副其实。
站在铁门关遗址前,尽管无“关”可穿,但我仍可以想见铁门关繁华竞逐的当年:城内一条大街通往人流穿梭、归帆去棹的码头,一条通向方石砌成、鱼鳞黑瓦、飞龙图壁的龙王庙。街上商号栉比,酒肆、钱庄、货栈、旅店,号幡斜矗;龙王庙、关帝庙、土地庙、财神庙,建筑森然罗织。云淡残阳之下,戏楼锣鼓铿锵,唱腔杳杳缈缈;天地辽阔之间,佛寺香火缭绕,青烟直上云霄。更有烟馆、赌局、妓院,门外楼头,犬马声色,悲恨相续,一时难歇。乡民商贾,置地经营;百工居肆,辛劳兴业。然而,这座傍海土城却抵挡不住黄河的泛滥淤积,清末,所有建筑沉没地下,丰国、永阜亦不再产盐,海上交通断绝,铁门关曾有的辉煌就此衰落,千户居民徙走大半,余者只能弃商从耕。据说,前关村小学西侧曾有同治十三年第三次大修铁门关时高二米余的捐款碑顶露出地面,不知尚在否?只可惜那上下两层、松柱支撑、花格木棂、金粉敷顶、高耸华丽的大戏楼再也难觅踪迹,那盏暴雨之夜拯救船队于惊涛骇浪的龙王庙“神灯”,也已被浩渺的大水熄灭,只留下它曾赋予铁门关以“神关”之名的传说,偶尔出现在老人们记忆模糊的念叨中……
“铁门锁浪”。我一直在琢磨这四个字的力道与雄健。汀河的铁门关内控黄河,外锁海运要津。岂止海运,定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被铁门锁住的浪头,怕也不止喻指盐、商、渔之利与患的角力,大抵还有民生安定与动荡间的平衡。
然而,在数度被淹、屡遭重创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夺清”,又自铁门关入海。31年后的光绪十二年,黄河将铁门关彻底淹没,同年,码头遂迁至利津东关。铁门关终于没有锁住滔滔的黄河巨浪,而永远告别了人间。
当地百姓同时遭遇了与铁门关一样的命运,大水漫漶中,人们四散奔逃,无家可归,或葬身鱼腹,或棚居堤上,上演了一部凄绝的人间悲剧。
大水也将人们赖以劳作生存的一切都变作了“遗物”。在铁门关主题展馆里,我看到了许多遗留下来的旧物件,泛着陈年暗淡的光,乌黑的,生锈的,干裂的:船舵、木浆、独轮车、马提灯、提篮、水罐、鱼篓、鱼叉、拂尘、念珠、马镫、马鞍、马铃铛、量斗、算盘、秤杆、拉锯、刨子……也许很多来自地下,仿佛内部还闪动着水纹的毫光,表面留有阴干的水渍。也许还有很多来自当年的码头、土城与民居,散架的木船、倒塌的墙围、倾圮的宅院,将其封存经年。这些时光的“遗物”折射着遥远的光景和日常生活的流影,它们如破碎的镜片,再难拼接为一体,映照出一幅完整的沧桑画卷。然而,每一件旧物又都像一个时空漏斗,可以让人隐约窥见这片土地上人类曾经生存的岁月“景深”。
我相信,铁门关下一定还埋有更多历史遗物。它的意义远远超过考古的范畴,而是一部有待整合的历史大剧,不单传承这片土地的远古,更续接这片土地的今天和未来。作为渤海经大清河航运通往内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铁门关仍生动地“活着”,等待今人和后人不断回眸凝视的目光。
职工天地 2021年12月01日 星期三
走 近 铁 门 关
《职工天地》(2021年12月01日 第A63版)

文王 川
在那片土地上游荡的时候,我注意到,很多人把目光投向汀罗镇的铁门关,那是利津历史上的第一名胜。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它早已被淤沙深埋地下,再也看不到一丝痕迹。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很可能会变作一个传说,变作后人心生遗憾的推测与想象。即使今天,它也已然变形为纸页上抽象的符号,只散存于县志和文史资料中,再不能从文字上耸立起来,与人们的推测与想象对接、呼应、印证。铁门关,如此坚硬的存在也能被时光破为齑粉吗?时间的力量真是强大。
铁门关何时建成,似无具体年代可考,若从金代算起,约有七百余年。当地有种说法:先有铁门关,后有利津城。这很符合人类因利而逐、因利而居的天性,何况此地所出,实有大利。而这里最繁华的时候当在明清两代,之前的铁门关,更多的功能在于海防。《利津县志》和《中国古今大辞典》均有记载,称其“金置,明设千户所,以资防御,有土城遗址”“形势雄伟”。金政府为控海滨之险,建筑土城,方圆近五里,四方各有巨大城门,门上有铁环、满布铁钉,“铁门”之称由此而来(据崔树梓口述、李钧整理《铁门关》)。其时,县城西北七十里的丰国镇濒临渤海,有自然盐沟,盐业发达,来往商船、渔船时停泊于此,铁门关便也兼有了航运码头的功能。“举棹而获鱼鲜,泛舟则获盐利。”加之关东三粮的输入,其贸易繁荣,自不待言。“蛎浦朝宗,济水达于千里;铁门锁浪,沧海长于百川。”(《武定府志》)如此气魄伟阔、盐渔丰饶之地,怎能不富甲一方、强盛一隅?
多次去过利津,“铁门关”是当地人口中频现的词汇,不断引发我的神往。有时候在茫茫夜色中散步,我会猜想铁门关在哪个方向、距我多远。会不会在我行走的乡路上或不远处,就有当年熙来攘往的人流与马车队前来经商、运盐的繁忙景象,他们如一溜烟云般出入铁门关口,嘈杂的吆喝、辚辚的车声和萧萧的马嘶缭绕不绝,响彻云霄。我想象着那些来自淄川的盐商许氏、来自杭州府仁和县的丰国盐场大使纪氏,还有无数外地盐民、盐商,将盐窝场、永阜场、丰国场、徐家天泉、韩家盐垣子、卢家盐垣子、金盆底等八大盐场和著名字号的白花花的盐源源不断地从陆路官道,或从穿过铁门关后的水旱码头输送到鲁西、豫东、皖北、苏北等地的浩大场面。舟船辐辏,客商若云,铁门关下一派繁忙的景象,仿佛仍在时空深处持续着。在史册中,我了解到,因为盐利,成就了季、董、卢、刘、岳、薄、盖、韩、徐、任、林、崔等盐商大户,更有日本、朝鲜、英国的商船来此贸易,引得内地无数的盐民源源不断迁徙到此。尽管至明中叶,土城残破,城中居民却从不足百户增至千户之多。“铁门”颓朽,挡不住沙洲芦滩变为边河大镇,寂寥汀渚摇身丰饶之乡。我想,铁门关虽然起初用以防备,其后却成了凝聚丰厚盐利的津门码头,利津之名是否得之于此?生“利”之“津”,真可谓名副其实。
站在铁门关遗址前,尽管无“关”可穿,但我仍可以想见铁门关繁华竞逐的当年:城内一条大街通往人流穿梭、归帆去棹的码头,一条通向方石砌成、鱼鳞黑瓦、飞龙图壁的龙王庙。街上商号栉比,酒肆、钱庄、货栈、旅店,号幡斜矗;龙王庙、关帝庙、土地庙、财神庙,建筑森然罗织。云淡残阳之下,戏楼锣鼓铿锵,唱腔杳杳缈缈;天地辽阔之间,佛寺香火缭绕,青烟直上云霄。更有烟馆、赌局、妓院,门外楼头,犬马声色,悲恨相续,一时难歇。乡民商贾,置地经营;百工居肆,辛劳兴业。然而,这座傍海土城却抵挡不住黄河的泛滥淤积,清末,所有建筑沉没地下,丰国、永阜亦不再产盐,海上交通断绝,铁门关曾有的辉煌就此衰落,千户居民徙走大半,余者只能弃商从耕。据说,前关村小学西侧曾有同治十三年第三次大修铁门关时高二米余的捐款碑顶露出地面,不知尚在否?只可惜那上下两层、松柱支撑、花格木棂、金粉敷顶、高耸华丽的大戏楼再也难觅踪迹,那盏暴雨之夜拯救船队于惊涛骇浪的龙王庙“神灯”,也已被浩渺的大水熄灭,只留下它曾赋予铁门关以“神关”之名的传说,偶尔出现在老人们记忆模糊的念叨中……
“铁门锁浪”。我一直在琢磨这四个字的力道与雄健。汀河的铁门关内控黄河,外锁海运要津。岂止海运,定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被铁门锁住的浪头,怕也不止喻指盐、商、渔之利与患的角力,大抵还有民生安定与动荡间的平衡。
然而,在数度被淹、屡遭重创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夺清”,又自铁门关入海。31年后的光绪十二年,黄河将铁门关彻底淹没,同年,码头遂迁至利津东关。铁门关终于没有锁住滔滔的黄河巨浪,而永远告别了人间。
当地百姓同时遭遇了与铁门关一样的命运,大水漫漶中,人们四散奔逃,无家可归,或葬身鱼腹,或棚居堤上,上演了一部凄绝的人间悲剧。
大水也将人们赖以劳作生存的一切都变作了“遗物”。在铁门关主题展馆里,我看到了许多遗留下来的旧物件,泛着陈年暗淡的光,乌黑的,生锈的,干裂的:船舵、木浆、独轮车、马提灯、提篮、水罐、鱼篓、鱼叉、拂尘、念珠、马镫、马鞍、马铃铛、量斗、算盘、秤杆、拉锯、刨子……也许很多来自地下,仿佛内部还闪动着水纹的毫光,表面留有阴干的水渍。也许还有很多来自当年的码头、土城与民居,散架的木船、倒塌的墙围、倾圮的宅院,将其封存经年。这些时光的“遗物”折射着遥远的光景和日常生活的流影,它们如破碎的镜片,再难拼接为一体,映照出一幅完整的沧桑画卷。然而,每一件旧物又都像一个时空漏斗,可以让人隐约窥见这片土地上人类曾经生存的岁月“景深”。
我相信,铁门关下一定还埋有更多历史遗物。它的意义远远超过考古的范畴,而是一部有待整合的历史大剧,不单传承这片土地的远古,更续接这片土地的今天和未来。作为渤海经大清河航运通往内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铁门关仍生动地“活着”,等待今人和后人不断回眸凝视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