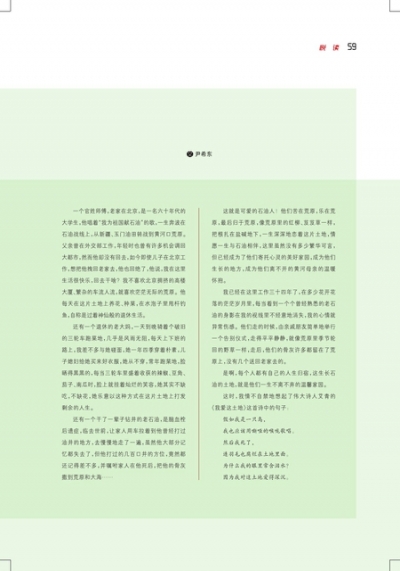文尹希东
这片土地,在中国偌大的版图上只是一个小点点,也许放大多少倍才能看得到。
然而,当你看到地图上那条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滔滔向东流入渤海,就不能光想象到河海交汇、亲吻的壮观景象,在这里还有由黄河泥沙填海造陆,冲积出的一片片新淤地。黄河岁岁不停地奔流,新淤地年年不停地向海里延伸。这片新土地,从地图上看只是一个点,然而在石油工人的眼里却很大很大,广袤无垠,莽莽苍苍,无边无际。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石油人,他们一辈子都走不出地图上的这个“点”,当他们把青春贡献给了高高的钻塔、滚滚的石油之后,就像黄河三角洲湿地里的无数鸟儿一样,在这里休养栖息了。
无论是春天、夏天、秋天,每当看到镶嵌在楼前楼后或是荒原草地里的一小片、一小片的菜园时,我就止不住地心生感动,为那些生长着的绿绿的菠菜、青青的蒜苗、翠翠的小葱而感动,为那些退休后还在这片土地上忙碌着的老石油们所感动,一处处篱笆,一片片菜园,点燃着他们心头的希望,辉映着他们晚年的夕阳。
与其说,他们是以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打发晚年的生活,不如说是他们以这种特有的方式守护着内心的一片家园,更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一种寄托和眷恋。当初,他们把这里当作了人生的起点,如今又把这里当成了人生的最后归宿。这片由大海、黄河围成的扇形荒原,虽然远离东营市区,乃至几十里看不到有人居住的村庄,甚至一直荒凉到渤海岸边,但他们对这片家园的眷恋,已经像地下炽热的石油一样,深深地燃烧在了自己的心里。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了石油,从他们走出故乡参加工作来到荒原上直到退休,算起来也有几十年了。在他们的心里,这片土地早已成为了第二个家乡,这里养育了他们终生不变的亲情,这里养育了他们终生不变的石油情,他们像“游牧部落”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游来游去,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喝惯了黄河水,吃惯了黄河水孕育的粮食和大海里那些海蛤子、海蟹子,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就对这片土地心生了深深的眷恋。
他们宁愿守护着旷野寂静的小小菜园,也不去那些繁华的大都市去感受喧闹。
我认识一个赵姓老石油,他是七十年代初从繁华城市青岛来到这片荒原的,工作四十多年退休后,有人说,青岛山青水秀,风景那么美,回老家去多好,多去享享晚年的福。他却说,在荒原上呆了一辈子了,心里再也离不开了。他前几年回家曾经住一段时间,却总感觉住不习惯,山好水好,不如荒原好,他说这辈子再不回去了。
一个官姓师傅,老家在北京,是一名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一生奔波在石油战线上,从新疆、玉门油田转战到黄河口荒原。父亲曾在外交部工作,年轻时也曾有许多机会调回大都市,然而他却没有回去,如今即使儿子在北京工作,想把他拽回老家去,他也回绝了,他说,我在这里生活很快乐,回去干啥?我不喜欢北京拥挤的高楼大厦、繁杂的车流人流,就喜欢茫茫无际的荒原。他每天在这片土地上养花、种菜,在水泡子里甩杆钓鱼,自称是过着神仙般的退休生活。
还有一个退休的老大妈,一天到晚骑着个破旧的三轮车跑菜地,几乎是风雨无阻,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我差不多与她碰面,她一年四季穿着朴素,儿子媳妇给她买来好衣服,她从不穿,常年跑菜地,脸晒得黑黑的,每当三轮车里盛着收获的辣椒、豆角、茄子、南瓜时,脸上就挂着灿烂的笑容,她其实不缺吃,不缺花,她乐意以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打发剩余的人生。
还有一个干了一辈子钻井的老石油,是脑血栓后遗症,临去世前,让家人用车拉着到他曾经打过油井的地方,去慢慢地走了一遍,虽然他大部分记忆都失去了,但他打过的几百口井的方位,竟然都还记得差不多,并嘱咐家人在他死后,把他的骨灰撒到荒原和大海……
这就是可爱的石油人!他们苦在荒原,乐在荒原,最后归于荒原,像荒原里的红柳、芨芨草一样,把根扎在盐碱地下,一生深深地恋着这片土地,情愿一生与石油相伴,这里虽然没有多少繁华可言,但已经成为了他们寄托心灵的美好家园,成为他们生长的地方,成为他们离不开的黄河母亲的温暖怀抱。
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三十四年了,在多少花开花落的茫茫岁月里,每当看到一个个曾经熟悉的老石油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不经意地消失,我的心情就异常伤感。他们走的时候,由亲戚朋友简单地举行一个告别仪式,走得平平静静,就像荒原里季节轮回的野草一样,走后,他们的骨灰许多都留在了荒原上,没有几个送回老家去的。
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归宿,这生长石油的土地,就是他们一生不离不弃的温馨家园。
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伟大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中的句子: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职工天地 2023年07月01日 星期六
为什么挚爱这片石油的土地
《职工天地》(2023年07月01日 第A59版)
文尹希东
这片土地,在中国偌大的版图上只是一个小点点,也许放大多少倍才能看得到。
然而,当你看到地图上那条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滔滔向东流入渤海,就不能光想象到河海交汇、亲吻的壮观景象,在这里还有由黄河泥沙填海造陆,冲积出的一片片新淤地。黄河岁岁不停地奔流,新淤地年年不停地向海里延伸。这片新土地,从地图上看只是一个点,然而在石油工人的眼里却很大很大,广袤无垠,莽莽苍苍,无边无际。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石油人,他们一辈子都走不出地图上的这个“点”,当他们把青春贡献给了高高的钻塔、滚滚的石油之后,就像黄河三角洲湿地里的无数鸟儿一样,在这里休养栖息了。
无论是春天、夏天、秋天,每当看到镶嵌在楼前楼后或是荒原草地里的一小片、一小片的菜园时,我就止不住地心生感动,为那些生长着的绿绿的菠菜、青青的蒜苗、翠翠的小葱而感动,为那些退休后还在这片土地上忙碌着的老石油们所感动,一处处篱笆,一片片菜园,点燃着他们心头的希望,辉映着他们晚年的夕阳。
与其说,他们是以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打发晚年的生活,不如说是他们以这种特有的方式守护着内心的一片家园,更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一种寄托和眷恋。当初,他们把这里当作了人生的起点,如今又把这里当成了人生的最后归宿。这片由大海、黄河围成的扇形荒原,虽然远离东营市区,乃至几十里看不到有人居住的村庄,甚至一直荒凉到渤海岸边,但他们对这片家园的眷恋,已经像地下炽热的石油一样,深深地燃烧在了自己的心里。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了石油,从他们走出故乡参加工作来到荒原上直到退休,算起来也有几十年了。在他们的心里,这片土地早已成为了第二个家乡,这里养育了他们终生不变的亲情,这里养育了他们终生不变的石油情,他们像“游牧部落”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游来游去,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喝惯了黄河水,吃惯了黄河水孕育的粮食和大海里那些海蛤子、海蟹子,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就对这片土地心生了深深的眷恋。
他们宁愿守护着旷野寂静的小小菜园,也不去那些繁华的大都市去感受喧闹。
我认识一个赵姓老石油,他是七十年代初从繁华城市青岛来到这片荒原的,工作四十多年退休后,有人说,青岛山青水秀,风景那么美,回老家去多好,多去享享晚年的福。他却说,在荒原上呆了一辈子了,心里再也离不开了。他前几年回家曾经住一段时间,却总感觉住不习惯,山好水好,不如荒原好,他说这辈子再不回去了。
一个官姓师傅,老家在北京,是一名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一生奔波在石油战线上,从新疆、玉门油田转战到黄河口荒原。父亲曾在外交部工作,年轻时也曾有许多机会调回大都市,然而他却没有回去,如今即使儿子在北京工作,想把他拽回老家去,他也回绝了,他说,我在这里生活很快乐,回去干啥?我不喜欢北京拥挤的高楼大厦、繁杂的车流人流,就喜欢茫茫无际的荒原。他每天在这片土地上养花、种菜,在水泡子里甩杆钓鱼,自称是过着神仙般的退休生活。
还有一个退休的老大妈,一天到晚骑着个破旧的三轮车跑菜地,几乎是风雨无阻,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我差不多与她碰面,她一年四季穿着朴素,儿子媳妇给她买来好衣服,她从不穿,常年跑菜地,脸晒得黑黑的,每当三轮车里盛着收获的辣椒、豆角、茄子、南瓜时,脸上就挂着灿烂的笑容,她其实不缺吃,不缺花,她乐意以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打发剩余的人生。
还有一个干了一辈子钻井的老石油,是脑血栓后遗症,临去世前,让家人用车拉着到他曾经打过油井的地方,去慢慢地走了一遍,虽然他大部分记忆都失去了,但他打过的几百口井的方位,竟然都还记得差不多,并嘱咐家人在他死后,把他的骨灰撒到荒原和大海……
这就是可爱的石油人!他们苦在荒原,乐在荒原,最后归于荒原,像荒原里的红柳、芨芨草一样,把根扎在盐碱地下,一生深深地恋着这片土地,情愿一生与石油相伴,这里虽然没有多少繁华可言,但已经成为了他们寄托心灵的美好家园,成为他们生长的地方,成为他们离不开的黄河母亲的温暖怀抱。
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三十四年了,在多少花开花落的茫茫岁月里,每当看到一个个曾经熟悉的老石油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不经意地消失,我的心情就异常伤感。他们走的时候,由亲戚朋友简单地举行一个告别仪式,走得平平静静,就像荒原里季节轮回的野草一样,走后,他们的骨灰许多都留在了荒原上,没有几个送回老家去的。
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归宿,这生长石油的土地,就是他们一生不离不弃的温馨家园。
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伟大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中的句子: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